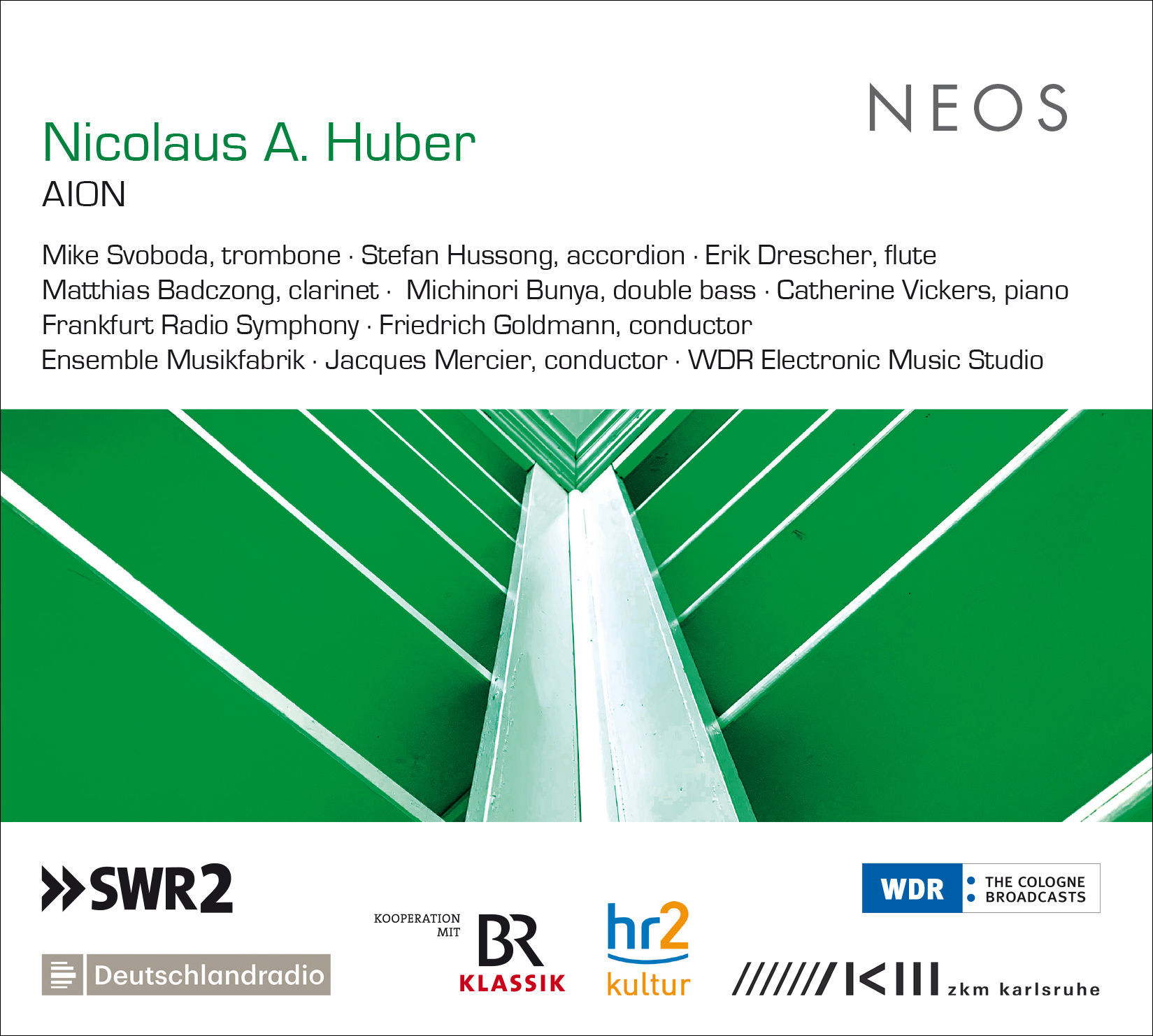信息文本:
NICOLAUS A. HUBER AION
当我作曲时,我总是想到听众。 我自己是我的第一个也是经常听众。 但首先我总是想到声音。 他们面对我,也以他们丰富的形式如声音、噪音、位置。 在这首曲子中,有些音调的音量不是他们自己的,但他们用它们来请求我们听众的注意,甚至乞求他们。 我认为,她的主要自我是她的长度。 只有当你用开放的耳朵接收到这些长度时,你才会体验到个性、视角、渴望和音调世界。 还有很多优雅、转瞬即逝的音调,一种跳频:»Angel Dust«。 就在我开始为 Naomi Klein 的恐怖书作曲之前,我遇到了这个词 休克策略, 其中开头描述了完全破坏人格的心理冲击尝试(中央情报局/美国和 E. Cameron 博士/蒙特利尔)。 含有 LSD 和 PCP(苯基-环哌啶-哌啶)的药物鸡尾酒也属于这些解耦尝试。 这种 PCP 也被称为“天使之尘”。 事实证明,去硬币后重新硬币和重新硬币是不可能的。 只是灾难性的人格毁灭。 然而,这对当今美国(仅?)酷刑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相比之下,音乐就是小菜一碟! 它具有与现实不同的现实主义。 这包括他们的自由! 该剧的所有事件都被锁定在一个 80 x 13 的比例结构中,但在新的划分中不断移动。 基本和声结构并不总是与句法结构一致。 结果,声音失去了清晰度。 你获得了非本地化的机动性。 而一个事件(A)在开始和结束(B1/B2)都被抓住的禁闭模型就变成了滑落和逃逸的复调运动过程。 现实作为音乐现实主义的推动力。 辩证法? 联络人?? 你的证人,亲爱的听众!!! 白色和绿色 为长笛和单簧管而作 (2018) 白色和绿色 是为降 B 长笛和单簧管而写的,没有任何乐器变化。 标题本身来自 Carmen Herrera,他在 1950 年代末画了几幅大幅面的画作。 它们都是具有两种颜色的建筑抽象绘画风格——在本例中为白色和绿色。 两种颜色都让我着迷了很长时间! 白色是马拉美用来写字的颜色,就像萨蒂后来写他的成绩一样。 绿色 - »le rayon vert« - 是马塞尔·杜尚 (Marcel Duchamp) 为 1947 年在巴黎举办的超现实主义展览而创作的神秘装置的颜色。 绿色的疯狂之处在于可以将它与音乐联系起来,因为只有当每秒有 5 个光子进入我们的眼睛时,我们才能看到绿色。 这是一个简单的四分之一 = 1 的五元组。这就是为什么 »60« 在我的作品中扮演特殊角色的原因 – 不仅仅是每秒! 这件作品还有一些奇怪的地方——5:1 或 2:1 或 4:1 的比例。 八度以这样的方式将音调加倍,使它们既可以合并又可以显示独立性甚至独立性,甚至可以微调地拉伸和弯曲八度。 Hermann Pfrogner 将这种神秘的关系验证为“I-interval par excellence”,“内部直立运动”,然后弦的划分进行到第五和第四。 所以我的二重奏包含一种特殊的二元性。每一个二元性都可以成为一个»1«,一个新的单位,一个新的»2«落入其中。 实际上是一个自由的,甚至是无限的增长结构。 在其中,一些音调回头看,仿佛量子纠缠,我们的感知器官对同时瞬时的距离和延伸感到惊奇,没有距离和延伸,仍然必须应对地点的概率波。 量子颜色——白色和绿色? 没有荷尔德林 为低音提琴和钢琴而作 (1992) 没有荷尔德林 是为萨尔布吕肯音乐节“20 世纪的音乐”而创作的。 两种乐器之间声音混合和声音融合的多种可能性是最重要的,直到“桌后尾声”以“极端暴力”结束工作。 与近年来的几部作品相比(秋节, 前进, 打开片段, 荷尔德林的精神错乱) 这件作品管理着“没有荷尔德林”,也使自己远离了一种荷尔德林时尚。 我的问题本质上要小得多,即以这样一种方式处理两种不同的声音,例如低音提琴和钢琴,从而创建一个声音整体,其中各个声音成分以有意义的方式相互证明. 当然,声音的结构也属于它。 所有结构都从小节结构、可直接识别的节奏、节拍数等中获得权威。 这首曲子显然是基于有机发展背景下的音乐思想。 然而,它的创作如此透明,以至于可以在平等的基础上体验个体,就像旋律中的音程、音程中的音调、音调中的声音、声音中的音量、音量中的曲线、音量中的曲线曲线的持续时间等。只有在最后,在表尾声的后面,透明度才会加剧到极端暴力,直到一声巨响。 面对面 为大型管弦乐队和磁带而作 (1994) 我的管弦乐作品的标题 面对面,意思是“相反的相反”,可以追溯到古埃及绘画和浮雕艺术的表现原则。 他们的表现密度是通过避免偶然的、统一的瞬间印象而获得的。 各个部分(例如人体)的连接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发生。 图片并不反映眼睛所见,而是通过将一组身体部位(眼睛、上半身、肚脐)相对于其他部位移动 90° 的技术——期望观众看到更复杂的事物。 这种同步的轮廓和正面视图允许更大的完整性,不遵守一次性注视捕获的时间限制。 立体主义的艺术家们重复使用了这些过程,并将它们进一步推向了碎片化和增殖的最大可能性(当然是为了他们的艺术关注)。 一张脸当一张脸是一个美妙的构想。 然而,在音乐中,最明显的重复方式作为可识别的东西将过于原始和短视。 在我的作品中组织音乐和管弦乐复杂性的技术可能最好用思想/思路的“多重表示”一词来描述。 这个道理交织在一起,交织在一起,分开,时间上散开,不同程度的接近和距离等等,很容易想象,也意味着它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你再也无法辨认出任何主要或次要的东西,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融合,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讲述一个故事,等等,那么就会出现一种新的聆听方式:原本连贯的东西突然之间只相互对立。 这种陌生感要求:对立面看到自己与对立面。 录音表演是最基本的想象方式。 整件作品分为 16 个部分,这些部分相互叠加。 这种同时按下的乐曲再次被分成两半,它们像两个耸肩(“耸肩”的乐曲)一样在实际(现场)乐曲之前和之后,可以这么说,就像两个巨大的延音。 阿尔戈 为钢琴而作的 AION 后奏曲 [带旋律和竖琴] (2019)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处理量子行为与谐波概念之间类比的可能性。 1968年我创作了磁带片 AION,其主题基础是荣格的原型理论,即。 H。 一切基于原型能量过程的事物都是 »tonal« 的。 对诺诺来说,调性被认为是包罗万象的,是“统一性的问题”。 这种对自我和作文的激进批评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当我最近读到 Wolfgang Pauli 和 C. G. Jung(1932-58 年)之间的通信时,我更加震惊了。 量子物理学家泡利从量子物理学的世界中观察了荣格原型。 他甚至创造了“背景物理学”一词,典型地产生了思维。 非局域性和概率波、没有特定位置、被认为是非因果但有意义的同步性、测量中没有独立的观察者等等——世界突然交织在一起! “Algol”这个名字也出现在这本书中。 来自阿拉伯语 al-gul(= 恶魔),这描述了一个亮度不同的双星系统,第三颗星围绕其运行。 位于英仙座的一颗变星,其亮度呈周期性波动,被称为“魔鬼星”。 在这个突然而完全出乎意料地在我身上爆发的充满活力的世界里,我有钢琴曲作为我的尾声 AION 组成。 那时我就知道原型是无法克服的,但意识可以创造一种距离。 现在是一个像 VR 护目镜一样的单人飞行游戏...... 玫瑰色拉维 合奏和磁带 (2000) »Rose Sélavy«,Marcel Duchamp 的第二个身份(仅从 1920-41 年开始),也是 »Rrose Sélavy«。 这来自杜尚在毕卡比亚斯的签名 L'Oil Cacodylate,它挂在酒吧 »Le Bœuf sur le Toit« 上,原文为:»Pi Qu'habilla Rrose Sélavy«(与:Picabia l'arrose c'est la vie)相同。 根据杜尚的说法,人们也可以这样理解:french、fresh、widow、window……八块方格的玻璃上覆盖着黑色皮革,“实际上应该每天早上像一双鞋一样打蜡,这样它们才能像窗玻璃一样闪闪发光”。 (杜尚在接受 P. Cabanne 采访时) 我真的对这个很感兴趣!! AION 四声道磁带和气味 (1968 / 72) 除了极少数例外,每个声音事件在 AION 中只出现一次。 他们的意义背景将他们捆绑到某些层次,并融入原型能量过程的主题张力控制中。 怎么样 AION 听? 无论如何,该作品已于 1968 年起草,旨在作为声学工作文件。 尼古拉斯·胡贝尔 程序: CD 1 [01] 天使之尘 长号和手风琴 (2007/08) 15:39 迈克·斯沃博达,长号 首映式现场录制
现场录音 [03] 没有荷尔德林 为低音提琴和钢琴而作 (1992) 15:47 Michinori Bunya,低音提琴 [04] 面对面 为大型管弦乐队和磁带而作 (1994) 18:38 法兰克福广播交响乐团
CD 2 [01] 阿尔戈 为钢琴而作的 AION 后奏曲 [带旋律和竖琴] (2019) 14:45 [02] 玫瑰色拉维 合奏和磁带 (2000) 19:25 首映式现场录制 [03] AION 四声道磁带和气味 (1968/72) 37:23 WDR电子音乐工作室
第一次录音 新闻评论:
神秘的星座 “只有每秒 5 个光子进入我们的眼睛时,我们才能看到绿色。 “这是一个简单的五连音,1 季度 = 60。这就是为什么‘5’在我的作品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Nicolaus A. Huber 在他 2018 年的长笛单簧管二重奏“Blanco y verde”的评论中写道。作曲家的一句话。他怀着永不满足的好奇心,从最偏远的地区寻找灵感。 在本双专辑的作品中,他发现它们来自杜尚的超现实主义、古埃及人、CG 荣格或左翼艺术家最喜欢的敌人——邪恶的美国人。 就像这里一样,他将大部分音乐之外的冲动敏锐地转化为音乐结构。 他考虑的高度抽象将流入作品的现实转化为神秘的声音星座,从而阻止了与节目音乐的任何联系。 这不会影响具体的声音外观——相反,这些数字具有精确计算的可塑性和色彩,它们将其识别为自主音乐过程的结果。 当前新版本中的作品创作于 1968 年至 2019 年间,因此代表了 Huber 作品的横截面,提供了丰富的说明材料。例如,管弦乐作品《Enface d'enface》:紧张的时间延伸和残酷的爆发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只遵循其自身规律的声音戏剧。或者钢琴曲“ALGOL”:在这里,量子物理学和原型理论的推测性结合创造了琴键声音和钢琴内部声音的复杂交织,从而导致了幽灵般的混响。胡贝尔的声音宇宙似乎在不断扩大。 马克斯·尼弗勒
13.07.2022 Quanta 和其他原型 十二生肖中的永恒之塔 Composing字面意思是“拼凑”、“拼凑”。 然而,人们想知道,那些不喜欢重复已经听过的东西的当代艺术音乐作曲家是从哪里得到他们的音调的。 每个作曲家对每首曲子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 就 Nicolaus A. Huber(生于 1939 年)而言,他的一些作品发表在“AION”CD 上,声源不一定是可听见的,但 Ernst August Klötzke 描述了它们。 这张双 CD 的标题是从 Nicolaus A. Huber 录制的最古老的作品中借用的。 “永恒之塔”不仅是标题,也是 1968 年至 2019 年间创作的不同演员作品合集的座右铭和结尾。 1990 年代初,音乐学家乌尔里希·迪贝柳斯 (Ulrich Dibelius) 称胡贝尔有“尾声强迫症”。 通过这句话,他暗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 Huber 的全部作品中,最后对作品的内在材料进行了总结,不仅是为了总结它,而且还开辟了新的视角,就像 Musil 的“可能性感”一样。 这种对正式部分的双重占用可以——这就是“永恒之塔”再次发挥作用的地方,它是双 CD 上的最后一部(尾声)同时也是最古老的(格言)作品——转移到胡贝尔的基本观点上,其中要检查的现象从来没有被孤立地看待,但总是在有时令人惊讶的联系中被背景化。 永恒之神代表了一种非线性的时间概念。 如果你从我们的经验出发,即时间事件的线性序列,那么非线性时间模型允许所有因果关系从他们熟悉的和直接的上下文中分离出来。 这种思维方式将 Huber 的音乐描述为声音的上层结构和下层结构,其效果是可听的,并且可以在物理意义上感受和体验。 通过这种方式,他在大距离之间创建了近距离(例如钢琴上等音的重新解释的音符代表最大可能的接近度(因为相同的键),同时最大可能的和声距离)。 Huber 的“主题”围绕着人,他们的行为、感受、思想和知识可能成为音乐的起点。 七首长号和手风琴作品“Angel Dust”(2007/08) 中的第一首是阅读 Huber 在“decognization”一词下创作的作品的结果。 正如他在随附的作品评论中所写,他对中央情报局等机构进行的心理冲击实验很感兴趣,这些实验旨在彻底摧毁一个人的人格。 作曲家以这样的方式翻译这样的主题,在“Angel Dust”中,“……音量不是他们自己的音调,但他们用这些音调要求我们听众注意,甚至乞求他们”,示例性地改变了透视是必需的,通过它可以剖析每个声学事件,并将其各个部分从熟悉的环境和传统层次结构中分离出来。 在处理乐器及其类型以及时间作为声音存在与不存在的相互作用时,这在处理乐器及其类型时以一种出色而令人愉悦的排他性可以听到:音乐在其各个事件中似乎同时又熟悉又陌生。 十年后,Huber 为长笛和单簧管创作了二重奏“Blanco y Verde”(2018 年),他在其中看到了与绿色音乐的“可能关系”,并在小册子中写道:“......因为我们只看到当每秒 5 个光子进入我们的眼睛时呈绿色。 那是 1 quarter = 60 上的一个简单的五元组。”他接着解释说,数字“5”在他的作品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并从其可能的分布中推导出一个增长结构,这是“Blanco y”的设计原则之一佛得角”代表。 音色和停顿的相互作用变得清晰可闻,身份在能量上漂移,并以转变的品质反复聚集在一起。 这让人想起在视频会议中查询麦克风状态。 通常当屏幕询问我们是否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时,我们会说些什么。 然而,这个回答随即回荡出强烈的变化和扭曲,自己声音的特征被异化和混杂得面目全非。 我们可以称这种声音的离域部分光谱,Huber 在“Blanco y Verde”中称之为“量子纠缠”。 在 80 世纪 90 年代和 20 年代(也许是对诺诺的四重奏“Fragmente - Stille, an Diotima”的反应),许多荷尔德林场景被写出来。 Huber 也以他自己的方式在几部作品中处理荷尔德林,包括他命名为“没有荷尔德林”(1992 年)的低音提琴和钢琴二重奏。 第一张 CD 上的第三首曲子的特点不仅在于一个特殊的尾声(“桌面尾声”)结束了作品,而且还有 Huber 音乐直到 90 年代所熟悉的身体节奏数字(呃称之为“概念节奏组合”)作为结构载体和其他参数的光线束处于最中心。 1994 年,Huber 为大型管弦乐队和磁带创作了作品“En face d'en face”,它被放在第一张 CD 的末尾。 同样,有一个特殊的起始位置导致了作品的创作,并反映在标题中。 根据 Huber 的说法,这可以追溯到“古埃及绘画和浮雕艺术的表现原则”,他感兴趣的是图片并不反映眼睛所见。 他将侧面和正面视图的同时性理解为“更高的完整性,不拘泥于一次性一瞥的时间限制。”他将其组合为一个思想的可听“多重表示”,从而导致不同的交织音质。 色彩的精湛技艺代表了视角和情感的灵活性。 密码呢? 就是这样,这一次(看一下乐谱就知道了)是一分钟的:“由指挥安排的衰落庆祝活动。 声音的衰减不应该简单地是一个“结论”,而应该通过长度(量化韧性)获得结构的意义”——作曲家说。 Huber 在 2019 年创作了第二张 CD 开头的最新作品(“ALGOL Nachspiel zu AION for piano with air drawings and Jew's harp”)。 对 AION 的引用清楚地表明 Nicolaus A. Huber 的“主题”范围可以表示为波浪,其中从相应的最大扩展到扩展开始的跳跃总是可能的,甚至可能是必要的。 这导致音乐的能量充沛不仅如预期的那样在“fff”爆发中显现,而且在“ppp”中集中释放。 通过嵌入它们的参数,声音和声音连接变得可感知为空间距离。 ALGOL 是 AION 的“尾声”(尾声?),当时 XNUMX 岁的作曲家在他大约 XNUMX 岁时面对自己,结果是“反道林格雷”。 紧张在于时间的距离,这导致了技巧和某种解放的宁静。 同样,与 AION 一样,语言也发挥了作用;与 AION 不同的是,它现在更像是声音的载体,而不是意义的载体。 在 2000 年的合奏曲(带回放)“Rose Sélavy”(即第二首)中,Huber 与 Marcel Duchamp 打交道,后者的非同寻常的艺术一次又一次地让他着迷。 这首曲子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音乐联系的巨大开放性以及精致而叛逆的声音。 这是一首不会让你孤单,也不想被它留下的音乐。 每一个色调背后都隐藏着意想不到的东西,它越来越多地展现出一种在惊人的密度中有意松散的联系,由此密度和扩张程度都可以导致微妙的个体色彩。 尾声? 值得聆听和寻找。 好吧,最后是 AION (1968/72),与 CD 上的其他作品相比,它无疑可以被确定为早期作品。 它是为四声道磁带和气味编写和制作的,以处理 CG Jung 的原型为起点。 Huber 将 AION 命名为预期的“声学工作论文”。 然而,在 60 年代后期经常出现的表示所谓未完成的事物的语境中,AION 将自己呈现为——在 Huber 的开放意义上——一个封闭的作品。它创建的时间和它之间的巨大距离现在的问题在“不受保护”地使用语言方面尤为明显。 然而与此同时,这也使得两张CD上的合辑值得称赞,后来的胡贝尔,他呈现了一个多层次的人际关系网络,延伸到难以想象的距离。 Huber 的音乐源于聪明而善解人意的诠释者,他们用自己的头脑和心灵来聆听。 Catherine Vickers(钢琴)、Michinori Bunya(低音提琴)、Mike Svoboda(长号)、Stefan Hussong(手风琴)、Erik Drescher(长笛)、Matthias Badczong(单簧管)、Ensemble Musikfabrik(指挥)的录音和录音无一例外Jacques Mercier) 和 HR Orchestra(由 Friedrich Goldmann 执导)品质卓越,不仅体现了音乐的价值,而且与作曲不相上下! 这本只有作曲家作品评论的小册子很有帮助,因为——一如既往——目的是用文字扩大聆听空间。 听“AION”CD 时,脑海中浮现出克里斯塔·沃尔夫的“卡珊德拉”中的一句话,它作为非正式的尾声而变化:“让幸福打开了我的耳朵”。 恩斯特·奥古斯特·克洛茨克 |